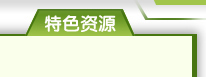爱丽丝始终保持她自己独立的私人生活,和她结婚的人必须明白这一点。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贝理却能够站起来迎接挑战。“最初的时候,我总是以为,表现出嫉妒会显得很粗俗,再说我也没有这样做的权利;可是一旦她察觉了它的存在,就会以她和我在一起时的那个‘自我’去抚平它,我马上就明白,她的这个‘自我’与她和别人相处时的那个人一点儿也不一样。”后来漫长岁月的生活似乎更加清晰地表明,“占有”在他们之间的关系中没有地位,贝理拥有爱丽丝与他相关的那一部分,而把她其余的部分留给她自己,留给她的工作,留给这个世界。
两人相识三年后结婚,婚后一直融洽。贝理说之所以能够如此,是因为两个人都天真单纯,不谙世故。这一对夫妇都对时尚没有兴趣,穿着随便,有时候甚至称得上糟糕,住的房子年久失修,做家务的能力都很差,可是他们能安然自得,看上去是得过且过,其实轻松自然,不为外物所御所累,这一点上两个人彼此欣赏,彼此感到愉悦。他们很少会想到要让世界顺从自己的意志,虽然两个人都成就不凡,却很难说他们有什么出人头地的愿望,甚至说不上有我们通常所谓的事业。他们有一个花园,一时兴起种植了玫瑰,尔后再也不去费心管理,很多玫瑰都死了,朋友戏称这座花园成了玫瑰的集中营。贝理却颇为自得荒废的花园倒还有活着的玫瑰,还说什么花瓣透明如纱,芳香浓烈似酒。
两人关系中最令人称奇的是各自保持、彼此尊重的美妙的“孤独”,贝理这样写道:我享受着婚姻中的孤独,并以为爱丽丝也这样看,这有点儿像自己一个人散步,同时却知道,明天,或者过一会儿,就会和另一个人一起分享,当然,也很可能明天或者过一会儿,还是一个人独自散步。这还是一种并不排斥婚姻之外的任何事情的孤独,反倒把感觉磨得更加敏锐,去感受与外面的事和人的亲密的可能性。
这不禁让人联想到里尔克的话,他在一封信中说,他不想失去他的孤独,却想把它交到良善的手里,这样,“至少我能够体会到孤独的某种连续性,而不用像一条叼着偷来的骨头的狗,在叫喊喧闹声中被追赶得四处乱跑”。“交流”一向被视为婚姻生活的法宝,需要认真对待,马虎不得;这一对牛津夫妇的交流却往往付之以玩笑的形式或片言只语,对于不能形之于言的部分有时或能心领神会,也有时不能理解却也不强求自己或对方理解。不刻意交流,而且在生活中为不能交流的部分保留出宽阔的自由空问。
贝理承认,在他们关系的早期,他对爱丽丝“知道”的越多,就越不能“明白”她,所以很快他就放弃了要去彻底“明白”她的想法,却也并不因此而生烦恼。爱丽丝拥有一个巨大、丰富和复杂的内心世界,在贝理看来反而是让他快乐和庆幸的事。有一次他们一起在意大利的托斯卡纳看彼埃罗的《耶稣复活》,贝理写道:这幅画迷住了爱丽丝。关于它,我们谈了许多,可是不论我们谈得多么多,我都清楚,它留给她的真正印象潜隐在言语的下面,就像冰山潜隐在水面之下。神自身的力量和存在的神秘强力驱使着他走出坟墓;这一形象未来将会激发出她自己丰富的想像和创造。
这一对夫妇有一项多年不变的显著爱好,就是相伴游泳。他们最常光顾的地方是牛津附近的一条河流,贝理回忆录的开头就描写了他们第一次去游泳的情景,不乏令人莞尔的笔墨。晚年遭逢病困,自然断了这一习惯。不过,回忆会把往日的情景拉到眼前,把眼前的生活照亮;在想像的河流里,爱丽丝和贝理还依然能够游泳——
坐在床上,身旁的爱丽丝确实睡着了,轻轻打着鼾。这样的平和真是美妙。我自己也再次迷迷糊糊起来,感觉像是顺河漂流,还眼看着从房屋里,从我们的生活里来的废弃之物——有好的,也有坏的—一在幽暗的河水里慢慢下沉,直到消失在深处。爱丽丝静静地在我身边漂流和游动。水面下,河草和大的枝叶摇曳,伸展。蓝蜻蜓在河岸边飞来飞去,盘旋悬停。突然,一只鱼狗一掠而过。
引文来源:献给爱丽丝的挽歌(读书乐之一)http://bbs.0513.org/thread-260823-1-1.html |